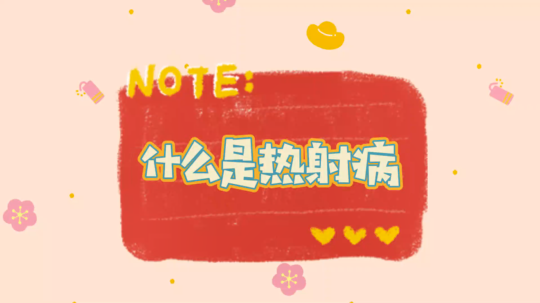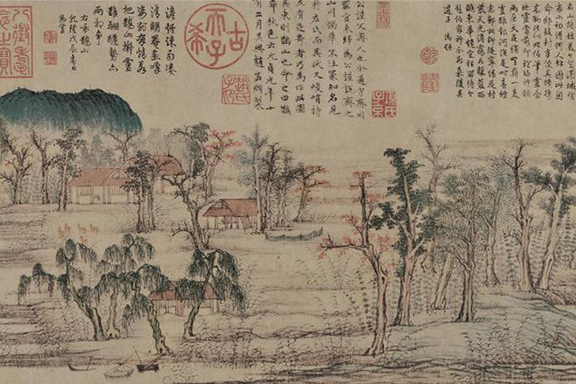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編號:33120190031 平陽新聞網 版權所有 中共平陽縣委宣傳部 主管 平陽縣融媒體中心(縣廣播電視臺) 主辦 浙ICP備13002923號
本站所刊登的各種新聞﹑信息和各種專題專欄資料,均為平陽新聞網版權所有,未經協議授權禁止下載使用
Copyright © 2018 www.cfj88.com All rights Reserved
平陽新聞網
王約與平陽社學
2022年10月11日 12:40:06
來源:平陽縣融媒體中心
陳斌 編輯王秀華
平陽自成化十四年(1478)創辦溫州第一所社學——賢祠社學后,直到弘治二年(1489)至弘治九年(1496)間,平陽知縣王約毀庵堂寺院,建社學。平陽社學數量增加了59所。當時,平陽社學數量列溫州首位。
社學的萌芽
洪武八年(1375)正月,朱元璋令天下皆立社學。后社學時興時廢,發展緩慢。正統元年(1436),明英宗下令在全國各地設提學官,每年對社學考校一次,要求每個鄉村興建社學。天順六年(1462),又下令創辦社學,免除教師勞役,并規定社學童蒙經考校合格,可補為儒學生員,但作用甚微。成化年間與弘治初期,由于社學稀少,鄉村百姓風俗澆薄。
在明代,江西社學極具代表性。一是其出現早,明代江西最早的社學記錄是洪武三年(1370),同治《九江府志》載,時彭澤縣知縣黃安泰建立社學。二是江西社學在天順年間得到較快發展。提學僉事李齡大力倡導社學,促成了多處鄉里社學的建成。弘治《撫州府志》、嘉靖《九江府志》、萬歷《南安府志》等記載,李齡在江西創辦的社學有44所(撫州府5所、崇仁縣4所、宜黃縣4所、樂安縣4所、金溪縣4所、豐城縣4所、德化縣18所、湖口縣2所、南安府1所、南安縣2所)。三是在江西各地興建社學過程中常常出現毀淫祠(歷代政府把不合國家祭祀原則的庵堂寺院定為“淫祀”或“淫祠”)與建社學并舉的情況,成化年間南安府知府張弼、弘治年間永豐知縣王昂均如此。
成化十四年(1478),平陽創辦賢祠社學。其作為溫州第一所社學,接受教育人數有限,影響不大。
社學的興建
王約任平陽知縣期間,結合江西社學創辦經驗,開展儒學民眾化教育,改變平陽陋習。道光《臨川縣志·人物》載:“王約,字資博,成化丁未進士,知溫州平陽縣。縣俗嫁女必厚費,葬必累石為高冢,以故民間多不舉女,率用火葬,約首嚴諭禁。毀淫祠六十余所,以建社學。”
王約,字資博,江西臨川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進士,弘治二年(1489)至弘治九年(1496)為平陽知縣。民國《平陽縣志》載:“王約……愛民禮士,首拓學基,葺治廟廡,建史伯璿祠,筑塘橋,徙壇壝,百度修舉。毀淫祠六十余所,建為社學。環縣置倉,倉實以谷。縣南三里置預備倉,谷至六萬斛。歲饑請發粟,當路不允,約曰:‘救民獲罪,所不辭也。’卒發之。重修本縣志……擢監察御史去,士民思之,祠于北津亭。”后任監察御史,先后巡查南直隸蘇州、松江與湖廣等地,再升云南副使。
王約創辦的社學有59所,即市心社學、仙壇社學、屏山社學、河頭社學、仕巷社學、旸坑社學、步廊社學、管奧社學、溪頭社學、涂瀆社學、竹山社學、金洋社學、浦邊社學、宋橋社學、周洋社學、練川社學、榆洋社學、宋埠社學、直湖社學、山邊社學、塘下社學、河口社學、豐山社學、鍾覺社學、白沙社學、仙居社學、儒橋社學、蘆浦社學、陳峰社學、藍田社學、荊溪社學、橫浦社學、龍岡社學、桂里社學、大覺社學、東安社學、東林社學、中亭社學、龍山社學、塘川社學、梅溪社學、新洋社學、南樓社學、靈峰社學、象灣社學、薦奧社學、三峰社學、儀山社學、峰頭社學、河口社學、塘下社學、昆山社學、新奧社學、鶴溪社學、南湖社學、江南社學、玉峰社學、岑山社學、錢倉社學。
關于王約在平陽建造社學的開始時間沒明確記載,但可從史料中發現蛛絲馬跡。乾隆《平陽縣志》載:“南津亭,在坡南。明弘治三年為社學,建房五間,有蔬園空地。今為僧茶寮。”故建造社學的時間應從弘治三年開始。
對于這59所社學何時創辦與何人創建,有些史料沒有明確記載。隆慶、順治、康熙《平陽縣志》只記載其名稱、所在鄉都及面積,并云“以上社學俱奉例立,師以訓鄉之子弟”。乾隆《平陽縣志》載:“以上社學,令王約奉例改庵立,師以訓鄉之子弟。其學址,今依弘治志補入。”隆慶、順治、康熙《平陽縣志》、萬歷《溫州府志》均載:“王約……毀淫祠六十余所為社學。”可見,這五十余所社學確是王約創辦。
這59所社學中,53所是從舊有的庵堂寺院改建而來,2所是“里人舍基為之”,2所是由其他場所改用或改建,即河頭社學(在坡南,弘治三年為社學,建房五間,有蔬園空地。)和錢倉社學(史伯璿祠)。還有2所沒有標明來源,即東安社學和南樓社學。
社學的經費可分創辦費用和日常支出。王約創辦的社學絕大多數是舊有庵堂寺院改建而來,故創辦費不多。社學的日常經費支出,即社師的廩餼與束修及貧困生的資助,應主要來自沒收的僧產與富戶的捐獻。民國《平陽縣志·風土志》載:“弘治間,令王約改諸梵宇之非敕建者為書院,即以僧產膳之,既而良有司次第設諸社學,富室復相感動,義學競設,弦誦之聲四境相聞。”至于是否收取學生的束修,文獻無記載。
社學的分布
社學,即一社之學。在明朝以十家為一甲,設一甲首。十甲成為一里,設一里長。里內舍有設祭,故凡設在里中之學,稱為社學。以洪武十四年所設的里甲制來看,一里有一百一十戶,即一里設社學一所。“里編為冊,冊首總為一圖”,故在當時又稱“里”為“圖”。民國《平陽縣志·食貨志》載:“明原額,通縣設隅一、都五十五、鎮二,共圖二百五十二。每圖立十甲,每甲貯田三百畝,充里一名。”弘治年間,由于三十八都、三十九都、四十都景泰年間析立泰順縣,二十四都久廢,故剩有圖二百三十二。
當時平陽縣有圖二百三十二,而王約創辦的社學只有59所,加上賢祠社學也只60所,故只有25.86%圖辦有社學。根據社學所在位置,分為在城社學、在鄉社學兩種。王約創辦的社學,屬于在城社學的,有市心社學、仙壇社學、屏山社學、河頭社學、仕巷社學,加上賢祠社學,在城社學共6所。1所在縣署旁邊,1所在東門城內,其余4所均在城門外(其中東門外1所、南門外2所、西門外1所)。據弘治《溫州府志·卷六·邑里》載,平陽“坊隅,附城內外,五圖。”可見,在城社學不僅每圖均有,而且個別街坊也有。在鄉社學共有54所,其分布為一都4所,二都2所,三都1所,四都2所,五都2所,六都1所,七都3所,八都3所,九都1所,十都1所,十一都3所,十二都3所,十三都2所,十四都2所,十五都3所,十六都1所,十七都2所,十八都1所,二十都1所,二十一都1所,二十二都1所,二十三都2所,二十六都3所,二十九都1所,三十二都1所,三十五都2所,四十一都1所,四十五都1所,四十七都1所,五十一都1所,五十四都1所。從社學的分布可看出,萬全、小南所有的都均設有社學,而江南、江西、南港、北港、蒲城片,還有12個都沒設立社學,這可能與這些地方地處山區、人口稀少或百姓不配合等因素有關。
社學的廢圮
王約創辦的社學廢圮于何時?隆慶、順治、康熙《平陽縣志》均載,“平陽故多文獻稱小鄒魯,嘉靖間倭寇剽掠,逃亡過半,鄉社廢弛”。可見,王約創辦的社學廢圮于嘉靖年間。而嘉靖《溫州府志》載:“平陽縣……社學四,俱在城。”嘉靖《溫州府志》完成于嘉靖十六年,故王約創辦的54所在鄉社學均在嘉靖十六年前,因倭寇侵掠平陽、百姓大量逃亡而廢圮。當時平陽在城社學還有4所存在,即仙壇社學、屏山社學、河頭社學、仕巷社學。而市心社學已于弘治七年毀于火,順治、康熙、乾隆、民國《平陽縣志》載,“市心社學,在市心街,舊普音堂,弘治七年火”。賢祠社學,應在弘治十七年撤并。民國《平陽縣志·神教志》載:“鄉賢祠,在先師廟門右。初在縣治倉前橋西首,為賢祠社學,祀宋、元、明鄉賢一十五人。弘治十七年,令李奎昭移建廟欞星門左。”隨著鄉賢祠遷至縣學,賢祠社學也隨之撤并。故嘉靖十六年平陽社學只有縣城的4所。這4所在城社學也在嘉靖中期停辦。民國《平陽縣志·武衛志》載:“(嘉靖)三十一年(1552)壬子春,海寇登岸劫麥城、錢倉、徑口、麻園,擄掠男女。夏四月,復劫九都江口。把總夏光與戰不利,賊益盛,遂至八都豐山、巖頭、塔下、陽奧各處,直抵仕巷,儒林所在,燒劫,時儒學方葺修,幾為所毀。”“(嘉靖)三十七年(1558)戊午端陽日,倭由瑞安渡江,至縣東,登仙壇山,射矢城中,燒劫南門外及嶺門,東西牌坊盡毀,喊聲震地。數日復燒東門。凡兩閱月,乃出,男女被殺及赴水者,不可勝計。”“(嘉靖)三十八年(1559)己未三月,倭寇南北交集,復至南門外,直入南北兩港,燒劫殺擄,男女及赴水墮崖者,不可勝數。”從嘉靖二十三年至嘉靖三十八年(1544-1559)的15年間,倭寇入侵平陽內陸8次。故這4所社學應毀于這個時期的倭亂。
社學的影響
溫州社學教育最早出現在平陽,即成化十四年的賢祠社學。弘治三年左右,王約又在平陽大辦社學。而溫州其他各縣的社學均在弘治十七年明朝廷頒發詔令后才開始普遍建立。歷代溫州府志對各縣社學的統計不同,但各縣縣志記載相對比較詳細。隆慶、順治、康熙、乾隆《平陽縣志》詳實記載了弘治年間王約創辦社學的情況。乾隆《溫州府志·社學》載:“地志于學宮多略,惟平陽志于學基、學田及社學、義塾畝分弓數確鑿具載可觀。”筆者查閱溫州各縣歷代縣志,并無創辦時間早于王約的社學。
王約創辦的社學只有59所,加上賢祠社學,不過60所,但可以說,當時王約是力圖初步普及平陽小學教育的。理由有四:一是當時平陽的總人口數為86162人。民國《平陽縣志·食貨志》載:“弘治,戶二萬七千一十五,口八萬六千一百六十二。”一般每所社學可以容納30至130學生讀書,取中值,以每所社學容納80名學生為準,60所社學可容納4800名學生。二是不僅王約創辦了社學,當時平陽的紳士們也創辦了許多義塾。民國《平陽縣志·學校志》載:“舊廢義塾。明。鄧林義塾在六都,里人林貴甫祠堂,弘治八年獻為義塾,撥田一十五畝。橫溪義塾在十三都,弘治五年,里人章民宰建,捐田二畝五分。金山義塾在二十都里人邱千二祠堂,弘治八年,獻為塾,撥田四十二畝。項橋義塾在二十二都項氏祠堂,弘治二年,項存顯率白石同族獻為塾,撥田六十畝。龍江義塾在二十二都黃判橋。梅江義塾在二十八都,義民陳文景建,又撥田三十畝。環塘義塾在三十二都,弘治九年,義民章仕昌建,撥田四十畝。北山義塾在四十二都陳氏祠堂,弘治八年,里人陳相率子侄創為塾,撥田四十畝。以上諸塾,已經勘結,延師設教,以田租贍塾之師徒。今俱廢。”這里記載的明代平陽義塾絕大多數是創辦于王約擔任平陽知縣期間。三是當時還有部分家塾的存在。四是即使一些圖沒有設立社學,其適齡兒童可去臨近圖的社學讀書。根據計算,當時平陽每個年齡段的適齡兒童應約為1120人,8到14歲的兒童應約為7800人。社學可容納4800人,占比61.54%,而義塾、私塾又可容納部分兒童,故可以說,王約是力圖在平陽普及小學教育的。乾隆《平陽縣志·建置志》評論道:“明中葉,王、萬諸公立社學百余,區歌詠之聲遍于閭里,其興也勃焉。”
王約在平陽大辦社學,推進了儒學教育的民眾化,有效改善了當時平陽的社會風氣,百姓移風易俗,讀書風氣大盛。民國《平陽縣志·風土志》載:“弘治間,令王約改諸梵宇之非敕建者為書院……弦誦之聲四境相聞。或有紈袴子弟夤緣進取,不但士類不齒,即農賈亦所不屑。幼嚴羞惡,長尚廉隅,所由來者漸矣。”
版權聲明:
凡注明來源為“新平陽報”、“平陽新聞網”的所有文字、圖片、音視頻、美術設計和程序等作品,版權均屬平陽新聞網或相關權利人專屬所有或持有所有。未經本網書面授權,不得進行一切形式的下載、轉載或建立鏡像。否則以侵權論,依法追究相關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