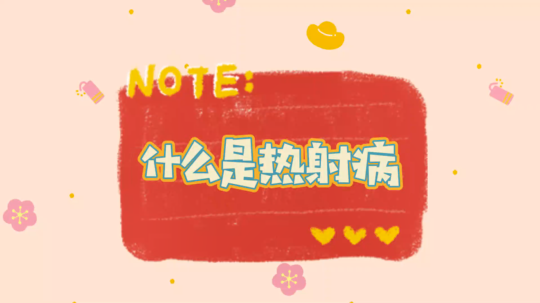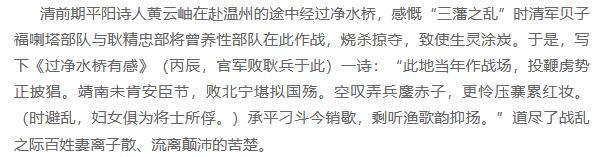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編號:33120190031 平陽新聞網 版權所有 中共平陽縣委宣傳部 主管 平陽縣融媒體中心(縣廣播電視臺) 主辦 浙ICP備13002923號
本站所刊登的各種新聞﹑信息和各種專題專欄資料,均為平陽新聞網版權所有,未經協議授權禁止下載使用
Copyright © 2018 www.cfj88.com All rights Reserved
平陽新聞網
空嘆弄兵鏖赤子 更憐壓寨累紅妝 ——黃云岫及其《過凈水橋有感》詩考略
2023年10月21日 09:10:29
來源:平陽縣融媒體中心
陳斌 編輯 王秀華
清前期平陽詩人黃云岫在赴溫州的途中經過凈水橋,感慨“三藩之亂”時清軍貝子福喇塔部隊與耿精忠部將曾養性部隊在此作戰,燒殺掠奪,致使生靈涂炭。于是,寫下《過凈水橋有感》(丙辰,官軍敗耿兵于此)一詩:“此地當年作戰場,投鞭虜勢正披猖。靖南未肯安臣節,敗北寧堪擬國殤。空嘆弄兵鏖赤子,更憐壓寨累紅妝。(時避亂,婦女俱為將士所俘。)承平刁斗今銷歇,剩聽漁歌韻抑揚。”道盡了戰亂之際百姓妻離子散、流離顛沛的苦楚。
一、黃云岫及靜觀樓
黃云岫,康熙、雍正年間平陽縣城西郭人,平陽諸生。他少年時跟隨平陽縣城東郭的歲貢呂弘誥讀書。呂弘誥為清初平陽著名學者,康熙甲戌年歲貢,主編過康熙《平陽縣志》。民國《平陽縣志·人物志》載:“呂弘誥,字克俊,一字宸書,東郭人。幼穎悟過人,弱冠入庠,試輒冠軍,經史子籍博覽淹貫,詩賦援筆而就。康熙甲戌歲貢,老困場屋,結社葛溪,門多知名士。年八十馀,手不釋卷。順治間,邑人貢生陳文謨為《縣志》八卷,康熙癸丑重修,至是弘誥輯為十二卷。著有《葛溪文集》《詩集》。”康熙三十七年(1698),呂弘誥受縣令王奕鵬邀請,擔任過平陽金印渡義塾的塾師。
黃云岫為呂弘誥得意門生。民國《平陽縣志·人物志》載:“(呂弘誥)弟子以詩名者,有黃云岫,字逸青,西郭人。由邑庠入監,沈潛力學,恬淡寡營,以詩禮持躬,雖盛夏,必衣冠見客。家構一樓,寒暑其上,晨夕苦吟,所著有《靜觀樓詩集》,邑令王元位為之序。”《東甌詩存》載:“黃云岫,字逸青。平陽諸生,著有《靜觀樓詩集》。【按】黃云岫,字逸青,平陽人。少從同鄉呂弘誥學,由縣學入國子監,屢試不利,乃隱居鳳凰山麓,以書史自娛。著有《靜觀樓詩集》。”黃云岫《靜觀樓詩集》中有《挽呂宸書夫子》一詩:“十載從游仰斗山,突傳一旦棄塵寰。樓中作記需才學,地下修文伴卜顏。八秩膺揚終未過,千年鶴化自空還。葛溪遺藁存吾黨,捧讀吞聲淚欲潸。”他在詩中悼念恩師呂弘誥,說自己跟隨呂弘誥學習過。
黃云岫居住的靜觀樓在九凰山北麓山下的平陽縣城西郭。民國《平陽縣志·古跡志》載:“靜觀樓,在西郭昆山麓,前臨龍湖。清黃云岫所居。”昆山即九凰山,民國《平陽縣志·輿地志》載:“錦屏山東南為昆山,雄麗峻拔,為縣城表鎮。頂上有巨巖,又名古巖山。山上舊有二木,冬夏常青。下空洞,可容數十人。西一峰曰南屏山。山自西迤東降為平衍,至街右,復環曲而西,別起陡峰,為九凰山。蘇伯衡《西枝草堂記》云:昆山中脊支而為九。故又曰九凰。”而龍湖,民國《平陽縣志·輿地志》亦載:“城外河分二支:一自龍湖南流,受昆山水,轉東出普濟橋。嶺門水北流入之。又逕安龍橋。沿城而東,折北出長青橋。與埭下河合。復分支東迤入東塘河,其干河仍北行,折西會北水門河,與北塘河合。”故推測,黃云岫的靜觀樓,就在九凰山北麓下的“大巖下”,此處恰好是“西郭昆山麓,前臨龍湖”。1985年版《浙江省平陽縣地名志》載:“大巖下路,位于九凰山北麓大巖下,故名。南接西坑路,西連欄桿橋路。全長120米,寬2米。”而《東甌詩存》所說的黃云岫“隱居鳳凰山麓”有誤,應是“隱居九凰山麓”。
黃云岫曾在縣學讀書,后入國子監學習,多次參加科舉考試,均未被錄取。他潛心研究學問,性情淡泊,為人處事注重禮儀,即使在盛夏季節有客人來訪,也必定穿上長衫、戴上帽子見客。時平陽縣令王元位為其《靜觀樓詩集》作序。民國《平陽縣志·職官志》載:“王元位,字升揆,吳縣人。進士。康熙五十年知縣,秉性仁慈,克己恤民。在任十四年,蠲減雜徭,民無他異,振興文風,詳請加額。去任之日,邑民聚哭于庭。”王元位在《靜觀樓詩集序》里云:“黃君逸青,年未弱冠補博士弟子員。呂宸書先生,昆名宿也,早從之游,為高弟。時藝、古文無不工,尤長于詩,乃數奇不偶,隱居凰麓,以書史自娛。山樓清勝,題曰靜觀。凡天地山川、昆蟲草木,興會之所流連,性情之所寄托,千匯萬狀,盡態搜妍,自新機杼,非同世俗掇古句、襲陳言、自號風騷者也。余下車即識逸青,恂恂儒服。后獲睹其詩文,始驚為博雅君子,然猶未窺全豹。今出茲集見示,選聲則金石鏗鏘,擷句則云霞絢爛,勝情幽趣,誠有得于靜觀之旨。回想昔年烹鮮斯土,未申薦剡,顧令文行兼優之士棲遲寤歌,不覺惶然愧云。”王元位對黃云岫的為人與學問評價非常高。
二、凈水橋不在平陽
瑞安孫延釗《明季溫州抗清事纂》云:“丙辰,海上稱永歷三十年、康熙十五年(1676)。……官軍敗耿兵于平陽凈水橋。”并注:“黃云岫《過凈水橋有感》詩注,見民國《平陽縣志》卷七十三。”孫延釗認為康熙十五年清軍與耿精忠部曾養性在平陽凈水橋發生戰斗,而且是根據黃云岫《過凈水橋有感》詩注推斷。
筆者查閱了隆慶、順治、康熙、乾隆、民國等《平陽縣志》,均沒有找到平陽有凈水橋,也沒有康熙十五年清軍與曾養性部在平陽發生戰斗的記載,故黃云岫詩中的“凈水橋”應該不在平陽。
那么,凈水橋到底在哪里呢?根據康熙丙辰年(康熙十五年,1676)清軍與曾養性部發生的戰事來分析,康熙十四年(1675),曾養性部敗退至溫州,康熙十五年的戰事主要是在溫州郡城附近進行的。《時變記略》載:“乙卯(1675)秋八月,曾養性忽疑溫州楊城守賣降,自黃巖罷師回溫,屠楊一門。徐大鼻亦自處州敗,罷師,皆退保溫州。大清師躡追至境,北屯太平嶺山,西屯凈水新橋山。……至丙辰(1676)五月,忽傳令班師,營壘盡撤。”《明季溫州抗清事纂》載:“丙辰,海上稱永歷三十年、康熙十五年(1676)。二月十七夜,曾營出所制火箭分與各兵,令埋伏于西山相近之佯岙凈嶼寺諸山下。二更時,潛師出三角(門)外,水陸齊進,投火燒清營盤。傅喇塔用大炮打沉曾船,于火光中登高,望見曾師紀律不整,遂用計誘敵即,令被燒下營移踞上營,謹守要隘。及曙,親督大軍下山交戰,曾師大敗,被追至將軍橋、灰橋等處,歸路斷絕,或溺或擒,喪失殆盡。都督孫可得、總兵副將李節、何賓等五百五十余人皆陣亡,吳旗鼓全家俱沒。養性墜馬,浮水逃入城中,堅守不出。五月,傅喇塔撤兵回處州,逐隊運炮,陸續啟行。至天長嶺,曾兵聚于毛垟坡對面山,傅喇塔以伏兵破之。行至靈福,曾師又于袋頭山攔截,泊船滿港,皆自瑞安、平陽新調而來,傅喇塔乃于靈福西州安營,潛運大炮至鳳樓山,復大破之。”
弘治《溫州府志》載:“崢水橋,在(永嘉縣)十五都。”“(永嘉縣)十五都:洋岙、崢水、岙上。六圖。”并注釋“周行己《浮沚集》卷四《介軒記》:‘佛者安時,避喧于崢水之上,’即此。明后‘崢水’多寫作‘凈水’,此志尚存古稱。”嘉靖《溫州府志·卷之二》載:“凈水(橋),俱在(永嘉縣)吹臺鄉。”上面所說的凈水橋在永嘉縣十五都或永嘉縣吹臺鄉,此地現屬于溫州市甌海區景山街道。所以,黃云岫《過凈水橋有感》一詩寫到的“凈水橋”應該是指現甌海區景山街道的凈水橋。
三、丙辰年凈水橋發生的戰事
丙辰年,即康熙十五年。黃云岫在詩注里寫道:“丙辰,官軍敗耿兵于此。”
康熙十三年(1674)三月,耿精忠在福建發起叛亂,以響應吳三桂。四月,平陽縣城發生兵變,向耿精忠部將曾養性獻納城池,浙南門戶大開,曾養性率部長驅直入,致使溫、臺、寧、紹諸地被曾養性部占領。康熙十四年八月,康親王杰書率領清軍主力入浙,和貝子福喇塔分兵征剿。康親王自衢州往福建,福喇塔自錢塘江渡紹興前往溫臺。福喇塔率軍進行黃瑞山之戰,陣斬曾養性部將陳鵬,收復天臺紫云山,取得首戰勝利。康熙十五年正月二十五日,副都統繆赫林、署護軍參領額庫納、齊林布、署參領禪拜在白水洋,擊敗曾養性部鎮海都督林沖。二月初一,奪取臺州府屬仙居城,生擒曾養性部都督僉事朱富,迫使曾養性、祖弘勛從臺州逃回黃巖。七月初十,清軍包圍黃巖縣城,曾養性、祖弘勛棄城逃回溫州。二十日,福喇塔率軍克取樂清。二十日從樂清出發,九月初三在上塘嶺的隘口,擊敗曾養性水師都督張拱垣3萬余眾。康熙十五年二月十六夜,曾養性、祖弘勛發兵4萬,從溫州水、陸進行反攻,福喇塔率領副都統吉勒他布、沃仲巴圖魯等滿洲、蒙古、綠旗官兵,迎戰于溫州城西,大敗曾軍于西山、將軍橋等地,陣斬曾養性部都督孫可得、總兵李節等官員300余人、士兵2萬余眾,曾養性幾乎被擒,逃入溫州死守。
《時變記略》載:“乙卯秋八月……大清師躡追至(溫州)境,北屯太平嶺山,西屯凈水新橋山。彼時乘勢近城,一鼓可下,但只擄掠子女,無取城意,鄉村為之一空,貞女觸巖、投水死不計其數。師至瑞安麗岙,麗岙子女亦遭擄。賊在郡,筑巽山白塔一帶御師,塘河橋梁皆毀壞絕渡。時人民驚疑,恐大兵恢復,玉石俱焚。幸王師不急攻城,惟溺于女色,屯住偃息。至丙辰五月,忽傳令班師,營壘盡撤。子女為所擄者悉驅北去,鄉都涂炭,后有往京、省贖回者。”乾隆《瑞安縣志·卷之十》亦載:“(乙卯八月大清師躡追至[溫州]境),北屯太平嶺,西屯凈水新橋,時兵馬四出打糧、驅掠婦女。永邑貞女觸巖、投水死不計其數。瑞安麗岙一帶亦然。賊在溫筑巽山白塔一帶御師,塘河橋梁自筼筜橋?吳田皆搗壞絕渡。時王師屯凈水,曾養性傾五邑之兵夜襲營,連焚二寨。黎明,元帥見賊兵無紀,縱馬逐之,賊大潰,盡溺凈水殲焉。……王師至丙辰五月卒然班師,營壘盡撤,所擄子女悉驅北去。后有往京、省贖回者。”可以看出,在福喇塔率領清軍包圍溫州時,曾駐扎在凈水橋,并在凈水橋與曾養性部交戰過。交戰的時間是在康熙乙卯年至丙辰年,即康熙十四年至十五年。清軍駐扎在凈水橋及其周邊時,紀律十分松懈,對百姓燒殺搶掠、無惡不作,造成妻離子散,民不聊生。
四、黃云岫其他描寫溫州的詩
溫州作為府城,黃云岫參加科舉考試要到溫州,赴國子監讀書也要經過溫州,故其在《靜觀樓詩集》中留下了數首描寫溫州的詩。
第一首為《郡城試后游仙巖贈天目和尚》:“戰罷風檐作勝游,名場暫撇入丹邱。尋僧初識千花面,拉友欣浮一葉舟。蓮社敲詩還索和,松間拂榻荷相留。上方領略無生諦,儒墨誰云道不謀。”此詩是黃云岫在參加了溫州的郡試以后,回程路上經過仙巖,與天目和尚相遇,寫下相贈。
第二首為《江心嶼懷古》:“中川形勝擅雄奇,梵宇年深巋舊基。駐蹕曾遺南渡跡(高宗南渡駐蹕于此),勤王空集北征師(文天祥募兵勤王)。梅溪書卷龍湫在(相傳王梅溪讀書寺中,有僧知其前身是龍,誘其書卷),桂海安瀾蜃怪移(甌海嘗有蜃氣,又名蜃江)。底事滄桑姑勿間,江城如畫且題詩。”此為懷古詩,黃云岫在游覽江心嶼時,聯想到宋高宗、文天祥、王十朋等曾在此處居住過,但滄海桑田,往事匆匆,令人感慨萬千。
“甌上流離劇可憐,幾番回首欲凄然。”黃云岫《過凈水橋有感》一詩,是其經過溫州附近凈水橋時觸景生情,有感于康熙十四年至十五年清軍與曾養性部在此處發生的戰事而寫,這場戰事造成了血流成河、生靈涂炭,而且清軍駐扎此地時,放縱士兵搶掠婦女,導致許多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給百姓帶來了無盡的苦難。
參考文獻
1. [清]曾唯輯,張如元、吳佐仁校注:《東甌詩存》,上海市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版
2. [清]從永清修、吳慶云等纂:《瑞安縣志》,中華書局,2012年版
3. [民國]王理孚修、劉紹寬等纂:《平陽縣志》,中華書局,2020版
4. 無名氏:《寧海將軍固山貝子功績錄》,中華書局,1991年版
5. 胡珠生著:《溫州古代史》,中國文史出版社,2019年版
6. 滕紹箴著:《三藩史略》,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
7. 劉鳳云著:《清代三藩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8. 陳光熙編:《明清之際溫州史料集》,上海市科學院出版社,2005年版
版權聲明:
凡注明來源為“新平陽報”、“平陽新聞網”的所有文字、圖片、音視頻、美術設計和程序等作品,版權均屬平陽新聞網或相關權利人專屬所有或持有所有。未經本網書面授權,不得進行一切形式的下載、轉載或建立鏡像。否則以侵權論,依法追究相關法律責任。